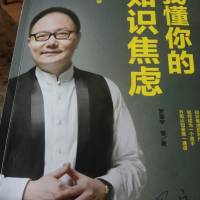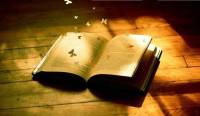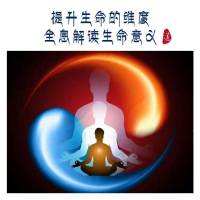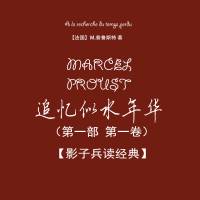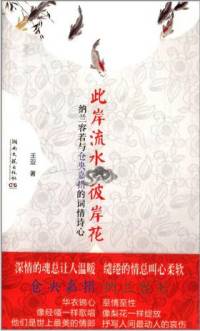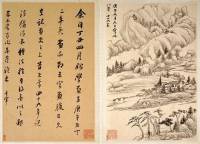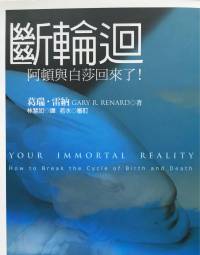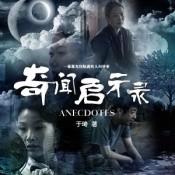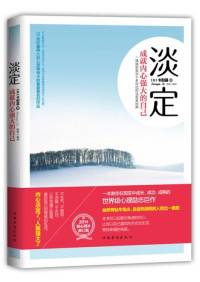-
-
状态:更新到27集
从求同存异到求同尊异,生命必须超越认知的局限;从求同尊异到归同了异,提升意识维度融合万有归一;从归同了异到无同无异,唤醒生命的终极圆满。
88.8万 2019-02-19更新 -
状态:完结 | 29集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(又译为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)是20世纪法国伟大小说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(1871~1922)的代表作,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的长篇巨著,以其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、宏大的结构、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卓越的意识流技巧而风靡世界,并奠定了它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。 法国著名传记文学家兼评论家A·莫罗亚在1954年巴黎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的《七星丛书》本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序言中写道:“1900年至1950年这五十年中,除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之外,没有别的值得永志不忘的小说巨著。不仅由于普鲁斯特的作品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篇帙浩繁,因为也有人写过十五卷甚至二十卷的巨型小说,而且有时也写得文采动人,然而他们并不给我们发现‘新大陆’或包罗万象的感觉。这些作家满足于挖掘早已为人所知的‘矿脉’,而马塞尔·普鲁斯特则发现了新的‘矿藏’。”这也是强调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艺术优点就在于一个“新”字。然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在于单纯的创新,也不在于为创新而创新,更不在于对于传统的优秀艺术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,从零开始的创新。创新是艺术的灵魂,然而创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,绝不是盲目的幻想。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的创新是在传统的优秀艺术基础上的发展。 法国诗人P· 瓦莱里和著名评论家、教授A·蒂博岱(1874-1936)都在他们的评论中夸奖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的艺术风格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。 安德烈·纪德和蒂博岱都提到普鲁斯特和十六世纪的伟大散文作家 蒙田(1533-1592)在文风的旷达和高雅方面,似乎有一脉相承之妙。还有别的评论家甚至特意提到普鲁斯特受法国著名的回忆录作家圣·西门(1675-1755)的影响。外国作家如 毛姆、 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 纳博科夫、 海明威等都曾高度评价过这部作品。
88.8万 2018-04-19更新 -
状态:完结 | 100集
纳兰容若,仓央嘉措。 我无法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,尽管他们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交集。 他们,一个在京城,一个在拉萨,一个是满清贵胄,一个是藏地诗人。 如果非得说他们有什么联系,那就是,在纳兰容若离世之前,仓央嘉措诞生了。他们共同朝奉一个君王——康熙,仅此而已。 可是,冥冥中,纳兰容若和仓央嘉措似乎又有着无法剥离的纠葛,也或者,只是我的心偏执了,硬生生要将他们扯在一块儿。 他们都是向佛的,所不同的是,纳兰因为爱情而虔诚,而仓央嘉措的虔诚,因为爱情而有了杂质。
88.8万 2020-04-03更新 -
状态:更新到21集
祈祷是敞开心门的手,祈祷是人类最伟大的声音,祈祷是与天地宇宙,万物一体沟通的桥梁。每天清晨,当阳光洒遍大地的时候,我们用真诚的祈祷,来开启一天的生活
88.8万 2019-01-12更新